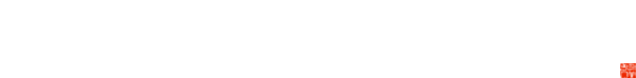2013年8月5日,收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王钧林教授邮件,告知今年是我们共同的老师李永采先生80华诞之年,也是他从教满65年之际,因此,准备为他出版《李永采教授从教65年纪念文集》,除选录先生各个时期的照片和代表性论文外,还拟收录曾受教于先生门下的各时期员工写的纪念性文章。王教授在邮件中说,在谈及请哪些同学撰文时,先生提出由我写一篇。闻此,我惶恐又倍感荣幸。惶恐,在于自己不算是一个好员工,与先生提及的其他学长相比,实在没做出什么成绩;荣幸,在于先生在诸疾缠身多年且近几年又经历几次中风的情况下,还能记得我。记得,即是一种莫大的关心。
一
与先生相识是在1996年的9月。当时,我从临沂师范专科学校专升本到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大学三年级。系里为我们专升本班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门《世界古代史专题》,任课老师即是李永采教授。记得第一节课时,先生身穿深色中山装,手提一黑色提包,落座后, 有条不紊地从提包中拿出讲义,然后笑眯眯地环视一下同学们,自我介绍道“我叫李永采 ……”然后开始讲课。在先生这一学期的课堂,我知道了什么是“血亲复仇”、“对偶 婚”、“从夫居”、“走婚”、“坐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这些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学术概念及其内涵。
除上课时间,先生还喜欢在课外与同学们聊天儿,聊学习、聊生活、聊人生、聊社会,有时也会聊及他的“右派”经历和学术观点。张安福、赵尊义和我最爱与先生的这种聊天,时常和先生边在校园中散步边聊。走累了,就在草地上席地而坐或坐在小花园中的长椅上继续聊。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聊天”真是一种令人享受的老员工活。
1997年暑假,我为准备考研究生而留校学习。记得一天下午5时左右,我、邱志方、沈素敏和张国昌等几位同学在教室看书,先生进来与我们闲聊一会儿后,微笑着问我们复习紧张不紧张,辛苦不辛苦。我们回他说不辛苦。国昌同学则戏言说“辛苦倒是不辛苦,只是肚子没油水,老想吃肉”,引起一片笑声。笑过后,先生说:“好,不耽误你们时间了,你们好好看书吧!我出去再转转就回家吃晚饭了。”但走后没多久,先生又回来了,从他的黑提包中慢慢拿出一包猪头肉、一包猪耳朵。说“我今天出来时带的钱不多,这些就暂且给你们打个牙祭吧!哈哈!好,你们慢慢吃吧,我回家吃晚饭了。”那是我所吃过的一顿终生难忘且时常回想和怀念的肉。
1998年3月,我接到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硕士生入学考试复试通知。先生即从其藏书中找出蒋孟引先生主编的《英国史》以及其他几本南大世界史专业老师写的书借给我,让我作针对性准备。待复试结束回到曲阜后,我对先生说,同其他几位一同复试的同学相比,尽管自己笔试成绩比较高,但却没有什么优势,差距比较大,对未来的研究生学习生活有些悲观。先生宽慰我说,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同别人之间的差距,本身即是一种进步 。你能考取笔试第一名,说明你的基础不错,只要你入学后虚心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和社会活动能力,将来一定不会差的。他还对我说,读了研究生,以后就步入学术研究领域了。在同学界前辈和同辈的交往中,待人接物一定要谦虚,但在学术研究上则不必谦虚,认为对的就要大胆坚持,就要大声讲出来。他并举了自己在大学三年级时即写文章 ,对自己老师童书业先生的观点提出质疑与批评的例子。
曲师两年,先生是给我关心、帮助最多的一位老师。他关于做人、做事、为学的教诲 ,我受用至今。
二
离开曲师之后,与先生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书信电话联系仍然不断。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习与生活,我似乎也对先生形成了依赖,在取得一点小小进步时就禁不住要跟先生秀一下,在遇到烦心事、情绪低落时又会首先想到向先生寻求开导与安慰。每次同先生的书信或电话联系,总能获得满满的正能量。除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外,先生还多次以各种借口(让我帮他查阅资料,或让我参与他的书稿写作)给我经济上的资助。在我工作后结婚生子时,先生及时从邮局寄来不菲的礼金向我表示祝贺。
其间两件事值得重点提及。一件是在研究生入学不久,先生即写信给我询问是否愿意参加他的一本书稿的写作。我回信说愿意,很快先生即寄来了写作提纲和所需资料。当时先生正在思考有关知识经济的问题,嘱我负责“知识经济浪潮与当代私有经济”和“知识经济浪潮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及其未来”两章的撰写。此后大半年时间,我们的联系即以讨论书稿的写作为中心。在此过程中,先生从资料的使用、论述的逻辑、学术规范等多个方面给我全面指导。记得在谈到如何界定“知识经济”概念时,我跟先生说由于“知识经济”属于一种崭新的、有别于传统工业经济的新经济形态,仍是一种尚在发展中的、带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经济形态,要给它下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概念目前是很难的 ,或者说为时尚早,询问他该怎么办。先生回信说,既然如此,不妨介绍一下它的特点和其有别于旧的经济形态或传统的工业经济形式的方面,或许比给出一个不太全面的概念更能给读者一个对“知识经济”的认识。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最终完成了这两章内容的写作,总字数46000余字。交稿后,先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先生的肯定,给予我莫大的鼓励,坚定了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
另一件事是:2000年,我利用暑假到泰安泰山疗养院去看先生。先生见到我非常高兴,畅谈后,即带我、邱志方和沈素敏两位同学(他们先我两天到)到菜场去大采购,说要好好给我们补一补营养。记得当时先生特意买了小龙虾。回来后,先生即忙着为小龙虾“净身”,去须除肠,清洁虾腹,边做边给我们解说如何做小龙虾。那次,我不仅生平第一次领略了龙虾的美味,且还学会了如何做美味的龙虾。一位好的老师,总会在不同的方面使你受益。
读研其间,我和先生虽远隔千里,亦少见面,但先生的关爱却时时围绕着我,给我信心,给我坚持,给我动力。2004年,在博士毕业论文定稿时,我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段话,以感谢先生对我的关心与支持。“感谢我大学时的老师——曲阜师范大学的李永采教授。先生健康状况一直欠佳,常年在疗养院接受治疗,但他却始终关心着我的员工与生活,并给予我尽可能的帮助与支持。我的成长之路上,有他的心血。我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幸福快乐!”
三
2011年之前,虽多病缠身,先生的身体状况相对还是可以的,有时还能到外地讲学,并去上海参观了世博会。但之后的多次中风,使语言表达能力受到严重损害,辞不达意,听者很难明白他所要表达的意思。这致使我们不得不中断了持续十多年的电话联系与交流。有关先生的情况,我只能通过岸冰师姐(先生的女儿)和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师弟杨刚及山东师范大学的王钧林教授那里了解到一些。总的来说,都还是一些好消息。如,先生健康状况大有好转,在修订他以前出版的著作,准备再版;先生又一次从医院康复回家了;虽多次中风,但先生的思维仍清晰;先生开始着手准备编辑自己的文集等等。
2011年暑假,我决定去济南(岸冰师姐为他和师母高老师在济南买了新房子)看望先生。我先同杨刚联系,请他到时带我去看先生。到先生在济南的新家后,他家的护工已在楼下等我们。他说先生正在洗澡换衣服,让他到楼下来接我们。上楼进家刚刚落座,先生即从浴室精神焕发地走出来,紧紧抓住我的手,高兴得不得了。高老师在一旁说,你们李老师听说你要来,非常兴奋,非要自己去洗澡、刮脸、换衣服。这次的交谈因先生的语言能力受损有些不甚畅通,但先生对我及我小家庭的关心仍能让我明显地感受到。先生详细地询问了我爱人和孩子的情况。我给先生看我儿子的照片,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并表示希望在方便的时候能给他寄一张我小家庭的全家照。怕先生过于劳累,本想看望一下先生即走,但先生却一定要我留下来一起出去吃晚饭,并打电话给王力军、王钧林、顾銮斋等几位在济南的学长和老师,请他们来,介绍给我认识,说他们都是颇有建树的学者,希望我以后多向他们请教学习。王钧林和顾銮斋两位老师因去外地,只有王力军老师一人前来。那晚,先生吃了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高老师语)。
四
10月8日晚,我完成了上文的初稿,本想修改一下即发给王钧林教授。不料却在9日上午突然收到王教授发来的短信,告知先生已于该日9:30去世了。我立即给岸冰师姐发了一条短信,对先生的去世表示哀悼,并询问有关追悼会的安排情况,说想去送先生最后一程。岸冰师姐回短信说,安排在11日下午1:40在济南经十路的莲花山殡仪馆为先生举行追悼会,并说你们工作都忙,没时间就不要来了。我爸在去世前即已失去意识,走得没有痛苦,很安详。
11日上午,我自南京乘高铁赶往济南,在1时左右到达莲花山殡仪馆,见到了从全国各地赶来为先生送行的50多位在不同时期受教于先生的员工,他们大都是工作在高校中的著名教授学者。后来,曲阜师范大学老干部处王处长在致悼辞时还提到,因工作和时间关系,还有许多先生的员工因不能前来参加追悼会,专门发来了唁电,感念先生的培育之恩,对先生的去世表示哀悼。诸多史学界精英的到来,使先生的追悼会似乎成了一场史学群英会。
追悼会结束后,师弟杨刚感慨说,这么多员工前来为先生送行,足以说明先生的一生是多么成功。我非常赞同他的这一说法。
在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即发邮件给同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谭树林和郑安光两位学长,告知他们先生已永远离开了我们。谭树林回信说:“凡祥,谢谢你告诉此消息。李老师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待人极好,尤其对年轻老师和员工!愿他老人家一路走好!”郑安光回信说:“凡祥,听到这个消息很悲痛。前两天还和谭老师以及吕厚轩谈到李老师,没想到老人家这么快就永归道山。李老师道德学问垂范后辈,愿他一路走好!”
李老师,您一路走好!我们大家会永远怀念您!